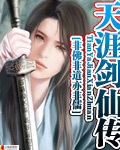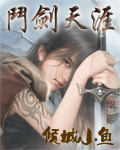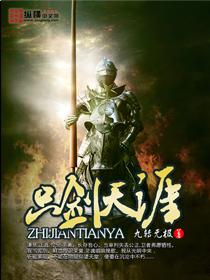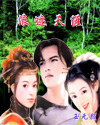天涯晚笛 听张充和讲故事-第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那时候,曲社都唱过什么戏?」
「就那么几出,《刺虎》、《游园惊梦》、《断桥》、《思凡》、《闹学》什么的。当时劳军,各部会联欢,唱的都是老戏,没有新编的戏。现在的小孩子,拉拉几天琴就要作曲了,就要编新戏了——弄音乐,哪有这么简单!」老人家忽然发起感慨来,「我在师范教戏,归在音乐系。执掌音乐系、同时在曲社里兼做文武场的,都是杨荫浏。他会弹琵琶,还会吹笛子。他把我唱的戏,都从工尺谱翻译成五线谱。先让一个姓叶的学生来翻,杨荫浏自己再做校对;然后让音乐系的学生去唱,让我再走一遍。他做得很认真,足足翻译了十个旦角戏,印出来给音乐学院做教材用,我这里还有当时的稿本。他用中国乐器来配,翻得很准确,注上各种符号,还写明『张充和的唱法』,听说后来还印成了书。」
杨荫浏(1899—1984),又一个中国音乐史上「如雷贯耳」的名字。今天一般的读者,也许无缘读过他著名的《中国音乐史纲》、《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和一系列关于中国民族音乐的著述,但是,一定都听过二胡曲《二泉映月》和古曲《满江红》。《二泉映月》这块中国民族音乐的珍宝,就是杨荫浏在一九五○年间,回到故乡无锡,亲自为盲人流浪艺术家阿炳录音、记谱而得以传世的;古曲《满江红》,则是一九二○年代由杨荫浏以现代简谱翻译古谱,并填上岳飞原词,才得以在民间广为流传的。
提起杨荫浏,张充和的神色变得活泼起来:「杨荫浏啊,他既是我的长辈,我们也是很熟很熟的好朋友。我们一起玩了很久,从云南一直到重庆。」
我注意到,提到昆曲、音乐和书法,老人喜欢用「玩」这个字眼。
「杨荫浏人也很好玩,典型的一个absent…minded(跑神,不专注),我们在昆明的时候就住得近,也在一起做事。记得那时候,他一天到晚在打算盘,我觉得奇怪,问他,他告诉我,他在计算音乐里的节奏。呵呵,他的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原来是在给音乐算节奏!」
中年时期的杨荫浏
屋子里,一时充盈着张先生的笑语欢声:「我到重庆以前,先在昆明做事,在教育部属下的教科书编辑委员会,跟沈从文、朱自清他们一起编教材,我管诗词、昆曲、音乐这一摊,沈先生管现代小说,朱自清管散文。那时候西南联大刚成立不久,沈从文同时在西南联大任教,我就和我三姐他们一家住在一起。我们花二十多块钱租了一个大佛堂,有四间小房可住人。前楼是沈从文一家,我住后楼;杨荫浏刚从后方来,住在旁楼;在西南联大管行政的杨振声,住另一个旁楼。我们几家人那时候吃、住都在一起。杨荫浏在昆明学校教音乐和算学,每天夹着个本子急匆匆跑去上课,房门永远不锁,见什么人都点点头,说:『对不起,对不起!』其实我知道他心里总是在想事。有一回我和杨振声、梅贻琦几个人,老远的跑到昆明学校去看他,他看见我们,点点头就走过去了,我们只好直接到他房间去了——他的房门永远开着的,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恍然想起我们是他的客人,慌忙从外面跑回来,连说:『对不起,对不起!』」
张先生说着呵呵笑起来,「杨荫浏研究的乐理方面的事情,我一点都不懂。他本来是学科学出身的,听说从前在燕京大学,他教的不全是文科,还有理科。他的笛子吹得很不错,经常为我们唱戏吹笛子,一板一眼的,很讲究。可他不会背曲,吹什么都得看谱,所以他把我唱的很多昆曲唱段都翻成了五线谱。他是很虔诚的基督徒,为很多赞美诗作曲,可是,他从来不向我传教。我的一个侄女当时和我住在一起,也信教,倒是一天到晚地向我传教。」
我插话问:「张先生,你有什么信仰吗?」
她笑笑:「没有。我不信佛,也不信上帝。从前带我长大的祖母倒是吃长素的佛教徒,心很诚的。可是我祖母从来不叫我信佛,也不要我吃素。她吃素,我在另一个小桌上吃荤菜。她的厨房都做素菜,唯一例外是给我炖汤,可以有荤的。」
这张富有代表性的张充和青年时代照片,即摄于一九三九年左右的云南呈贡云龙庵佛堂。
我知道我们又扯远了,就想拢回到重庆的话题上。
「我给你讲一个在重庆演戏,跟梁实秋和老舍有关的故事吧。」老人家喝了一口茶——她家里总是备有上好的当年新绿茶,据说是大陆亲友们每年都惦记着给她隔洋捎来的新茶。
「当时教育部新成立了个礼乐馆,在北碚。要唱戏,劳军演出,重庆的人都要下来帮忙。那次演出是教育部组织的,梁实秋、老舍当时在编译馆做事,答应两人要出一个相声;中央研究院物理所所长是丁西林,也懂音乐,他们负责搭台、装灯;我呢,就负责给唱戏的找配角。那场演出很盛大,来北碚的人很多,住不下的人都挤在礼乐馆里。那晚我演《刺虎》,正在后台化妆,梁实秋和老舍在边上练相声,一边练一边大笑,我就要他们先讲给我听听。老舍写相声很在行的,又是老北京,所以他是主角——逗哏的,梁实秋是捧哏的。排练时,有一个老舍举着扇子要打的动作,梁实秋说:『你到时别真打,比比样子就好。』结果到了台上表演,说到兴头上,老舍的扇子一挥,真的就打过来了,梁实秋没有防备,这一打就把他眼镜打飞了!梁实秋手疾眼快,一手就把眼镜接住了。下面掌声大作,以为是他们俩故意设计好的,就大叫:『安可!』『安可!』(再来一次)他们俩相对哈哈大笑,相声讲不下去啦……」
张先生轻声笑着,屋里的空气在欢快的回忆中跳跃着:「那一年到台湾,梁实秋跟我回忆起这一段跟老舍说相声的趣事,当时还录了音。前些年老舍的儿子舒乙到访耶鲁,我把这个录音和老舍与我的合照都让他带走了。这回(二○○七年春)我在北京开书画展览,舒乙在开幕式上讲了这个故事。可是他没讲对,我当场纠正他:当时梁实秋的眼镜没有被打掉,是打飞出去又一手接住啦!呵呵……」
张充和手抄的昆曲工尺谱
昆曲工尺谱
老人对细节的清晰记忆,从来都让我们这些晚辈叹为观止。
我问:「什么是礼乐馆?你刚才好像说,你后来是从青木关搬到了北碚?」
「我从教育部所在的青木关搬到北碚,就是从原来教育部属下的音乐教育委员会,调到了新成立的礼乐馆。礼乐馆的成立也有一段来由:重庆在孙中山先生的忌日纪念活动中奏哀乐。蒋委员长说不对,人死超过三年,就不该奏哀乐了。一个国家,礼乐都不通,该要制礼作乐了!教育部于是下了命令,要遵办此事。后来就成立了礼乐馆。连乡下人结婚的婚礼,也要制订证婚的礼乐仪式。乡下人礼拜天可以到礼乐馆来,按新式礼仪结婚,由公证人公证,杨荫浏还给弹个钢琴伴奏什么的,仪式很简单,但隆重。」
我记得,「蒋委员长」好像在抗战时期提出过「新生活运动」之类的口号,也许这新成立的礼乐馆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便问:「能给我说说礼乐馆的故事么?」
「国立礼乐馆直属教育部,馆长是汪东(汪旭初),礼、乐分开两组,卢冀野管礼组,杨荫浏管乐组,我是属于乐组的,负责做中国古乐,做外交仪式音乐,弘扬昆曲等国乐,从古诗里选出合适的诗词曲目做礼仪教化之用,等等。」老人又笑眯眯地提起一段佚事,「说起来,这个礼乐馆的馆长,还是我给保送的呢!教育部知道我跟沈尹默先生相熟,要我去请沈先生作礼乐馆馆长。我就去传话了。可沈先生说:『我不合适做。我只会闲里找忙,不会忙里偷闲,你去问旭初看看。我就去问汪旭初,一问他就答应了。他在北洋军阀时代做过相关礼乐的事情,当时是监察委员。他从监察院调到礼乐馆,也是个闲差使——呵呵,我这么说,倒把两个部都骂啦——我给自己找了一位上司,这位上司自然对我是很不错的。他亲自画了一本梅花送给我,可惜被我弄丢了。我当时二十多岁,他们管薪水的人,要在我的登记册上加几岁,这样可以领到平价米。我说我不要,他们说:『你不要我们要!』平价米可难吃啦,可那是战时,缺粮缺米呀!……」
我想象着那个战争年月,这位正在韶年、俏皮聪慧的张家四小姐,在教育部礼乐馆一群「国粹」长者中间穿梭来去,恰如烽火旧宅、战场废墟间绽放的春兰秋菊,其受到众星捧月般的疼爱、娇宠,也是不难想见的。难怪每提到重庆岁月,老人眉额间,总会掠过一片霞彩呢。
「搬到北碚以后,日军轰炸反而不多了。我们礼乐馆的防空洞又是最好的,离办公室很近,底下很深。我那段时间写了最多的小楷,一般都利用第一次防空警报拉响,而第二次警报还没响起来之间的时间。那段时间不算太短,正事反正是做不了了,写小楷不费墨,拿起笔来就可以写,直写到第二次警报响起才搁笔,几步就可以跑到防空洞去。待第三次警报响起来,日军的空袭才真正到了。」老人说起重庆轰炸的岁月,也显得云淡风轻的,「当时的重庆市长——名字忘了,是梅校长(梅贻琦)的学生,来青木关教育部看校长来了,遇到了日本人轰炸,当时就跟我和梅校长一起跑到防空洞去,结果防空洞的前半部分都给炸掉了,很危险。可是那时候我们到重庆会朋友,都是到教育部的防空洞里约会,想想也挺有意思。」
我很好奇:「那时候炮火连天的,你这么一个娇女孩儿,天天跑警报,害怕吗?」
老人微笑着摇头:「抗战时我也逃过难,没黑没白地赶路,但身体能挺得过去,给了我很好的经验,也没有什么担惊受怕的。飞机就在头上,要死就死,要活就活,习惯了,也就不害怕了。」
我说:「听下来,我觉得,重庆那段日子,是您一生中很有光彩的一段。」
老人微微颔首:「我那时候二十多岁,每个月领五十多块钱的薪水,还能资助我在昆明联大读书的五弟的生活费。那段时间我也交了最多的朋友。礼乐馆在嘉陵江边,江那边是复旦(大学)。我们要过水去,水很浅,可以走在石子上过水,不用小船。复旦我的朋友很多,年轻年老的都有:章靳以、洪深、方令孺——大家叫她方九姑,他们常常过江来找我玩,唱曲、写字、吟诗作画的,很热闹。我也常常过江去看他们,我过去,就住在九姑的家里。我前面提到的丁西林也是我当时最要好的朋友,我们算忘年交。四九年后他在中国政府里好像有一定的位置,他还给我和汉思写过信,劝我们回去。记得他写过一个关于妙峰山的几幕戏,寄出来让我把它变成昆曲,我还真的为它度了曲,可惜,再没有机会唱给他听了……」
老人陷入了久远的遐想之中。我记下了一个个在史书册页里熟悉的名字,又好似听见了潮拍江岸,在浪花激流间荡起的笙歌弦管的声音。
谈话于二○○七年九月十二日
二○○八年六月二十八日于康州衮雪庐整理毕
二○一○年秋经张充和校阅
「鱼玄机」与「桃花鱼」
张充和学诗的故事
案桌上摆着一本装帧精致的线装书——《唐女郎鱼玄机诗》。是一本新出的「中华再造善本」,按历代流传的宋版书重印的。翻开来,熟宣厚笃,版式古朴,顿觉雅意盎然,墨香盈屋。
充和老人告诉我:这是一位亲戚最近送的礼物,她很喜欢,常常倚靠窗边沙发,摩挲细读。讲起唐代这位女诗人鱼玄机的诗集,便讲到当初一位美国学生曾经为她精印的《桃花鱼》诗册。因为《桃花鱼》印数仅三百,很多诗友慕其名而难得一见,商求于我,我也不敢贸然问「鱼」于张先生。
张先生笑道:「那本诗册,用的是我自己誊写的小楷,印得精美而已,其实收诗不多,才十几首。我这些年写的诗,其实还从来没有结集出版过呢。我自己也疏于整理,写了就扔在那里了,很少人读得到。」
于是,我们便谈起女子学诗的话题。我说:「在从前那么一个男权和父权中心的社会,在男尊女卑的社会风气下,你的求学之路是怎样走的?女孩子学诗,会不会感受到什么压力呢?」
一九一八年在合肥, 张充和(左)五岁留影。(纽约海外昆曲社提供)
张先生手翻着鱼玄机诗集,吟吟笑着,向我说起她孩提时代学诗的经历来:「我祖母是我学诗的第一个启蒙人。祖母会做诗,能背很多诗。我五岁开始就跟着祖母背诗,读诗,每次还要把我读过、背过的诗似懂非懂地讲给祖母听。我出生八个月就离开了妈,跟祖母长大。祖母其实是我的叔祖母,她是李鸿章的侄女。她的父亲李蕴章,是李鸿章的四弟。」
我想起什么,问道:「张先生,这么说,您可以算是李鸿章的曾外侄孙女了?我记得张爱玲好像是李鸿章的曾外孙女,她祖父叫张佩纶,是李鸿章的女婿。你们这两个张家都来自安徽,有亲戚关系么?」
张先生笑笑说:「没有。我们和张爱玲不是一族的亲戚。他们是来自皖南的张家,我们算是合肥的张家。《清史稿》上记的我曾祖父张树声的传记,好像提到过曾祖与她祖父张佩纶有过什么关系。我没见过张爱玲,日常生活里也和他们的张家没发生过关系。李鸿章是安徽合肥人。合肥的李家和张家,是两个大姓人家。不过我们家,民国年后就搬到了上海,后来又搬到了苏州。」
「您是哪一年出生的?」我顺口问。
「一九一三年。就是民国二年。阴历是四月十二日,公历是五月十七日。现在很多书里提到我是一九一二年出生,是传错了。大概是当初结婚时候登记婚书的人,按中国岁数的算法,算多了一岁,就这样以讹传讹啦。」
这是我第一次「刺探」清楚了张充和的确切生日。这为我和孙康宜教授日后带上两位洋学生为她带来的那场「生日惊喜」,留下了伏笔。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