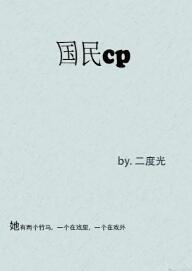林徽因传-第1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智记”。承安是金章宗年号,五年是公元1200年。至元九年是元世祖的年号,元顺帝的至元到六年就改元了,所以是公元1272年。这小小的佛龛,至迟也是金代遗物,居然在杏子口受了七百多年以上的风雨,依然存在。当时巍然站在杏子口北崖上的神气,现在被煞风景的马路贬到盘坐路旁的谦抑;但它们的老资格却并不因此减损,那种倚老卖老的倔强,差不多是傲慢冥顽了。西面墙上有古拙的画——佛像和马——那佛像的样子,骤着竟像美洲土人的TOTAM-POLE。
龛内有一尊无头趺坐的佛像,虽像身已裂,但是流利的衣裙褶纹,还有“南宋期”的遗风。
台基上东边的一座较小,只有单檐,墙上也没有字画。龛内有小小无头像一躯,大概是清代补作的。这两座都有苍绿的颜色。
台基前面有宽二米、长四米余的月台,上面的面积勉强可以叩拜佛像。
南崖上只有一座佛龛,大小与北崖上小的那座一样。三面做墙的石片,已成纯厚的深黄色,像纯美的烟叶。西面刻着双钩的“南”字,南面“无”字,东面“佛”字,都是径约八十厘米。北面开门,里面的佛像已经失了。
这三座小龛,虽不能说是真正的建筑遗物,也可以说是与建筑有关的小品。不止诗意画意都很充足,“建筑意”更是丰富,实在值得停车一览。至于走下山坡到原来的杏子口里望上真真瞻仰这三龛本来庄严峻立的形势,更是值得。
林徽因很仔细地画了素描,又落落大方地坐在杏子口北崖石佛龛的门口,把那件蓝上衣披在肩上,让梁思成为她拍照。
林徽因问梁思成:“你看这个佛龛像什么?”
梁思成说:“它很抽象,好像什么都像,又好像什么都不像,也许它只是一个符号吧。法国的郎香教堂像一艘驶向远方的大船,又像一顶荷兰牧师的帽子,也像祈祷合掌的双手,它们不是一般地实现了建筑的物质功能,而且在精神上、艺术上给人以强烈的象征性,建筑美的本质特征在于抽象,从广义上讲抽象就是象征。这两个佛龛,可以说它是扣在山顶上的僧帽。”
林徽因说:“不能孤立的看这两个建筑,它是整个山的一部分。在这个山口上,唯其朴素奇特,才能显示宗教的征服,这是蕴含在自然中的达观和庄严。”
平郊建筑的考察,唤起了林徽因特殊的审美感觉。1933年11月,林徽因、梁思成、莫宗江又到河北正定的兴隆寺、阳和楼、开元寺钟楼等10余处宋辽时期的古建筑考察。在她的眸子里,没有一块石头是冥顽不化的,而她的酬报便是那无穷的建筑意的收获。
彼岸的友情
一对新婚不久的美国青年,蓦然闯入了林徽因和梁思成的生活。他们便是后来成为著名社会学家、汉学家的费正清(费尔班克·约翰·金)、费慰梅(威尔玛)夫妇。
当时,费正清和费慰梅都是刚刚大学毕业的学生,费正清来自南达科他,费慰梅则来自麻塞诸萨州的剑桥,这一对如痴如狂的喜欢中国的人文历史和艺术的青年人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中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就是在那里相遇并相爱的。基于共同的爱好和追求,他们把自己的结婚地也选在了古老的北平。
在北平东城一座漂亮的四合院里,这一对来自大洋彼岸的年青人,怀着一腔新奇,过起了老北京人的日子。每天早晨他们到胡同口去喝豆浆、吃油条,挎篮子吆喝“箩卜赛梨”的小贩生成万物。万物变化不息,相因相革,人亦当对传统有所损,也引起他们极大的兴趣。每天,他们都会买上几只“心里美”箩卜,脆生生嚼出了一片地道的京韵。他们最喜欢做的一件事,便是坐上人力拉车,串北平的街道和胡同,那种古老的文化氤氲,让他们进入了一个古典的东方梦境。
他们找了中文老师,开始学习中国语言,神秘的方块字给了他们横平竖直的另一种语境。课余时间,他们便去紫禁城或香山的佛教寺庙里考察,但对他们更具吸引力的却是北平的门楼和城墙调和的产物,是阶级统治的工具,随着阶级的消亡,国家也,尽管这大墙内外上演着的一幕幕活剧,对于他们却还是那样陌生。
婚后的两个月,他们遇到了林徽因和梁思成,并从那时起,他们维系了一生血浓于水的友情。晚年的费慰梅回忆他们相识时的感受说:
“当时他们和我们都不曾想到这个友谊今后会持续多年,但它的头一年就把我们都迷住了。他们很年轻,相互倾慕着,同时又很愿回报我们喜欢和他们做伴的感情。徽(whei)——他为外国的亲密朋友给自己起的短名——是特别的美丽活泼。思成则比较沉稳些。他既有礼貌而又反应敏捷,偶尔还表现出一种古怪的才智,俩人都会两国语言,通晓东西方文化。徽以她滔滔不绝的言语和笑声平衡着她丈夫的拘谨。通过交换美国大学生活的故事,她很快就知道我们夫妇俩都在哈佛念过书,而正清是在牛津大学当研究生时来到北京的。”
往往真正的友情开始于心灵的奇遇,而这两对夫妇的相识却完全没有故事,他们在一次聚会上认识,并互相吸引,一交谈,才知两家居然是相距不远的近邻,这使他们喜不自胜。
新的友谊给林徽因的生命注入了新鲜的活力,当时她和梁思成刚刚由沈阳迁回北平,开始在中国营造学社的工作,百废待兴,而繁重的家事又给她凭添了若许烦恼,费慰梅怀念这段日子时记叙道:那时徽因正在经历着她可能是生平第一次操持家务的苦难,并不是她没有仆人,而是她的家人,包括小女儿、新生的儿子,以及可能是最麻烦的、一个感情上完全依附于她的、头脑同她的双脚一样被裹得紧紧的母亲。中国的传统要求照顾她的母亲、丈夫和孩子们,她是被要求担任家庭“经理”的角色,这些责任要消耗掉她在家里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
应该说,作为一个西方女性,费慰梅对林徽因的感知是深层次的,她在中西方文化的穴结点上,一下子找到了她的中国朋友全部痛苦的症结,费慰梅说:
“林徽因当然是过渡一代的一员,对约定俗成的限制是反抗的。她不仅在英国和美国,而且早年在中国读小学时都是受的西方教育。她在国外过的是大学生的自由生活,在沈阳和思成共同设计的也是这种生活。可是此刻在家里一切都像要使她铩羽而归。
她在书桌或画报前没有一刻安宁,可以不受孩子、仆人或母亲的干扰。她实际上是这十个人的囚犯,他们每件事都要找她做决定。当然这部分是她自己的错。在她关心的各种事情当中,对人和他们的问题的关心是压倒一切的。她讨厌在画建筑的草图或者写一首诗的当中被打扰,但是她不仅不抗争,反而把注意力转向解决紧迫的人间问题。”
林徽因把她的心扉全然向她的新朋友费慰梅敞开了。那段日子,费慰梅经常骑着自行车或坐人力车在天黑前到梁家去,穿过花园去找林徽因,两个人在起居室一个暖和的角落里坐下,并泡上两杯热茶,便开始了推心置腹的倾谈,她们有时比较中国和美国不同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有时谈文学艺术,并把对方不认识的朋友的追忆,毫无保留地告诉对方,林徽因谈得最多的当然是徐志摩,她给费慰梅大段大段地背诵徐志摩的诗,从她闪着泪光的眸子里,费慰梅读出了那一份深深地思恋。
很快费慰梅也同林徽因的那群朋友结成了知己,他便是逻辑家学金岳霖,大家都叫他“老金”,实际上他似乎是梁家的一个成员,他住在梁家院后一座小房子里,梁氏夫妇住宅的一扇小门,便和老金的院落相通。在梁家夫妇的聚会上,老金总是第一个到达的客人,有时这样的聚会也在老金家里举行。作为逻辑学家的老金,连同他幽默的性格也是那么独特,即使林徽因和梁思成一对小夫妻吵架拌嘴,老金也闻声过来解劝,从不问清红皂白,而是大讲特讲其生活与哲学的关系,总是迅速而有效地平熄“战火”,林徽因和梁思成也很佩服老金这理性的逻辑思辩。
经常参加聚会的还有坦率豪爽的政治学家张奚若和国际问题专家钱端升,不苟言笑的经济学家陈岱孙,在哈佛攻读人类学和考古学的李济,在伦敦留学的社会学家陶孟和等,也是这里的常客。应该说,那个年代梁家客厅里聚集的多是中国学术界的精英。
每到星期六,学者们的妻子也往往赶来参加聚会,费正清和费慰梅自然受到了大家的欢迎。他们的中文水平也就在这样的聚会中飞快地提高。
星期六的聚会,高潮是中午在饭店里的聚餐,差不多每次林徽因都给大家讲上一段开心的故事,而故事的主角儿往往是她自己。
有一个故事是这样的:林家的仆人陈妈,有一天惊慌地跑来报告说,在梁家西边的紧邻,房顶上裂开了一个大缝,因为在那居住的房客穷得修不起屋顶,托徽因向房东去求情,让房东出钱修房,林徽因马上去找房东,得知房客住的三间居屋每月只付50个铜板的房租,而且房客的祖上从乾隆年间就租用这处房子,已经200多年了,每月的房租是固定的,始终没有涨过,因此房东也没有能力出钱维修这座房子,事情的终结是林徽因给房东捐了一笔修理房顶费用才算了事。
大家都开心地笑起来。费慰梅像中国人那样,竖起大拇指,大声说:“徽,真有你的!”
不欢迎费氏夫妇的似乎只有林徽因的母亲和仆人们,老太太总是用一双疑惑的眼睛直盯着这一对黄头发、蓝眼睛的外国人。每当费氏夫妇扣响梁家的门环,开门的仆人总是只把大门打开一道缝,从上到下把他们打量一会儿,然后才把他们放进院子,而老太太却踮着小脚一直把他们追到客厅里,每次都是徽因把她的母亲推着送回她自己的屋里。
在林徽因心情不好的时候,费氏夫妇便拉上她到郊外去骑马,城市里的尘嚣被远远地隔在了灰色的城墙和灰色的心情之外,眼前出现的是另一种赏心悦目的景观。一望无垠的大平原上的庄稼,一直绿到城墙脚下,那蓬蓬勃勃的绿,散发出一种鲜嫩的气息。高高低低的土屋,错落在万绿丛中,远处的西山和北山,淡得如同一抹灰蓝色的烟迹,透过稀稀落落的树木,隐约可见远处的塔影。天空蓝得像一匹缎子,一丝丝云彩在小月河里漂荡着,元代的土城墙逶迤如一条灰蛇,起伏在纷乱灌莽中。
林徽因策马前行,她在马背上的坐姿真是棒极了,连号称美利坚骑士的费正清也叹为观止,林徽因信马由缰,沿着古老的灰色城墙,一会儿便纵马飞驰起来,她那条红色披巾,在风里飘荡如一团燃烧的火焰。
因为经常去骑马,林徽因索性买了一对马鞍,一套马裤,穿上这身装束,她俨然成了一位英姿勃发的巾帼骑师。
那段日子,带给林徽因的印象是新鲜而美好的,费氏夫妇回国后,她在信中对往事的回顾,依然是那样神采飞扬:
自从你们两人在我们周围出现,并把新的活力和对生活、未来的憧憬分给我以来,我已变得年轻活泼和精神抖擞得多了。每当我回想到今冬我所做的一切,我都是十分感激和惊奇。
你看,我是在两种文化教养下长大的,不容否认,两种文化的接触和活动对我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在你们真正出现在我们(北总布胡同)三号的生活中之前,我总感到有些茫然若失,有一种缺少点什么的感觉,觉得有一种需要填补的精神贫乏。而你们的‘蓝色通知’恰恰适合这种需要。另一个问题,我在北京的朋友年龄都比较大也比较严肃。他们自己不仅不能给我们什么乐趣,而且还要找思成和我要灵感或让我们把事情搞活泼些。我是多少次感到精疲力竭了啊!
今秋或不如说是初冬的野餐和骑马(以及到山西的旅行)使整个世界对我来说都变了。想一想假如没有这一切,我怎么能够经得住我们频繁的民族危机所带来的所有的激动、慌乱和忧郁!那骑马也是很具象征意义的。出了西华门,过去那里对我来说只是日本人和他们的猎物,现在我能看到小径、无边的冬季平原风景、细细的银色树枝、静静的小寺院和人们能够抱着传奇式的自豪感跨越的小桥。
隔着岁月的投影,费氏夫妇仿佛听到大洋彼岸那座古城墙下,疾风般的蹄鼓还在敲击着记忆的回声……
太太客厅
咚咚咚,一双陌生的手,叩打着北总布胡同三号四合院的门扉。
院子的女主人林徽因,最先听到了那健壮的骨节在门板上敲击出的怯生和窘促。
四合院的入口处有一个小院子,是仆人的住房。里边的院子一正两厢,北边正房是林徽因和梁思成的起居室,宽阔的门窗,镶嵌着林徽因精心设计的木格窗棂,上面糊了白色的窗纸,她把窗户的下层换成了玻璃,不仅可以透进阳光,还可以看到院子里的树木花草,屋顶是由鱼鳞状的灰瓦铺成。
她打开门,两张年轻的脸庞出现在面前。一个是沈从文,他是常客,已是蜚声全国文坛的青年作家;另一个却是陌生的,他大约二十出头年纪,微微泛红的脸上,还带着点稚气,他穿着一件洗得干干净净的蓝布大褂,一双刚刚打了油的旧皮鞋。沈从文介绍说:“这是萧乾,燕京大学新闻系三年级学生。”
“啊!你就是萧乾,《蚕》的作者,快进屋吧。”
萧乾用目光打量了一下这个院子。这是个不大的四合院,收拾得干净利落,院里有一棵丁香树,叶子还没有完全落尽,仿佛还留有残香,缕缕挂在枝头。
进了屋子,林徽因向萧乾介绍了刚从正定考察提前赶回的梁思成和来串门的北大教授金岳霖。
林徽因热情的给他们倒上茶。
来之前,萧乾看了林徽因给沈从文的邀请信,字里行间透着活泼和热情:
沈二哥:
初二回来便乱成一堆,莫名其所以然。文章写不好,发脾气时还要沤出韵文!十一月的日子我最消化不了,听听风,知道枫叶又凋零得不堪,只想哭。昨天哭出的几行,勉强叫它做诗,日后呈正。
萧乾先生文章甚有味儿,我喜欢。能见到当感到畅快,你说是